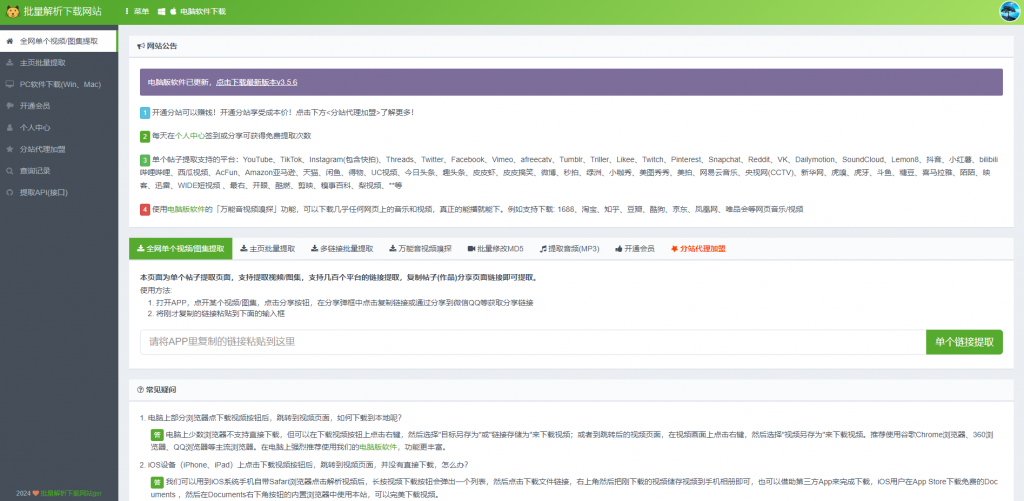第二天,机器人债务皇家委员会发布了它的报告。政府的做法再次受到谴责:在专员看来,这是粗暴和残忍的。受害者说他们“极度恐惧”,无法进食,“总是想着债务”。
许多澳大利亚人习惯于认为政府基本上是一个仁慈的力量。Azimitabar的判决和机器人债务报告让你稍微体会到,当政府的权力针对你时,它会有多么可怕。
机器人债务专员凯瑟琳·霍姆斯(Catherine Holmes)提出了一些经久不衰的观点:在我们的历史上,肯定很少有文件如此广泛地谴责一个政府的机制、文化、能力和良知,并通过大量具体失败的积累来证明这一点。
通读这份报告的建议,你会惊讶于这些建议是多么显而易见。领取福利的人不应该感到羞耻。弱势群体应该得到面对面的支持。政府应该检查新项目是否合法。政府不应该用欺骗手段来逃避法律建议。政府不应该随心所欲地将文件指定为机密。新项目应征求一线员工的意见。在重大变化方面,应征询顶级倡导机构的意见。公务人员应该得到适当的培训。
这份名单的纯粹基础性无疑加强了对上届政府的可怕判决。但鉴于政府已经不复存在,这些建议所描绘的更为重要的图景是,近几十年来,这种政府风格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常态。
在这种情况下,政治目标是第一优先事项;透明被本能地视为一件坏事;协商和合作被视为弱点;你所在政党以外的人都被视为潜在的敌人;预算节约和制度被认为比人更重要;公共服务已经内化了这种想法。
在这样的环境下,很多媒体往往放弃了对当权者的监督,转而成为对无权者的另一个折磨者。
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?
对于一份针对单一方案的报告来说,这个问题太宽泛了,但专员在序言中写道,她的建议的有效性将取决于两件事,这给了她一个至关重要的暗示。首先,只有当政的政府才能真正防止危机重演:最终,领导人必须定下正确的基调。
第二点是:政客们必须停止妖魔化福利接受者的“容易的民粹主义”。福尔摩斯在序言中提到这一点,这一事实凸显了它的重要性。这并不是说领取福利的人被妖魔化了,也不是说政府治理不力。对福利接受者的妖魔化使政府的失败成为可能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糟糕的计划在政治上是可取的;正是这一点让政府得以在政治痛苦最小的情况下坚持了这么长时间;正是这一点确保了该计划的残酷没有得到应有的媒体报道。
也许值得一问的是:如果这个计划没有被证明是非法的——如果维多利亚法律援助没有迫使政府承认这一点——我们大多数人会注意到这种残酷吗?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,因为在机器人债务的案例中,使该计划变得残酷的因素——平均收入——同时也是使其非法的原因。尽管如此,上周还是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对比。在Azimitabar案中,政府的行为也很残忍。但在那起案件中,它的行为被宣布为合法。不会有清算。
最后一点。在机器人债务报告出炉之前,上周的政治讨论主要由土著人之声主导。“讨论”是慷慨的。其中大部分是可怕的或欺骗性的。《澳大利亚金融评论》(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)上的一则广告显示,赞成运动者托马斯?梅奥(Thomas Mayo)为钱跳舞,正如新南威尔士州自由党议员马特?基恩(Matt Kean)指出的那样,这让人想起了吉姆?克劳(Jim Crow)时代的漫画。(它的所有者,也是这个报头的所有者,后来道歉了。)彼得·达顿(Peter Dutton)断言,总理对英国之声的痴迷是房价和抵押贷款上涨的原因;邦宁斯(Bunnings)等公司的价格正在上涨,因为它们向支持独立的运动捐款。
这里有两种观点。第一个,在广告中展示的,是一个种族主义妖魔化高调的土著人民争取赞成票。第二,在广告和达顿的言论中都可以看到,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的家庭预算与英国之声之间正在形成对立。
这听起来似曾相识,令人不安。当霍姆斯描述妖魔化福利接受者的“轻松民粹主义”时,她是这样描述的:“纳税人与福利接受者的叙事”。“反对”运动让土著活动家扮演了最近福利接受者所扮演的角色:施舍,让我们其他人付出代价。
这已经够糟糕的了。但福尔摩斯的观点涉及到一个更广泛的问题。太多的政治家没有投入到严肃而乏味的治理工作中——制定如何实施对人民生活产生(积极)影响的政策和计划——而是被一个更愚蠢的问题所引导:我们能提出什么样的政策,才能让我们与一个容易被诋毁的敌人进行一场民粹主义之战?
在目睹了机器人债务的后果后,我们的许多媒体和政治阶层都发誓“再也不会”。但问题不会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再次出现。轻视重要问题?妖魔化那些受够了苦的人?把政府变成一场好人和坏人的游戏?在美国之声的辩论中,这种情况已经再次发生了。
法律和程序是可以固定的。残酷是澳大利亚政治中一种更为持久的压力。这种情况似乎不会改变。
肖恩·凯利(Sean Kelly)是专栏作家,曾担任朱莉娅·吉拉德(Julia Gillard)和陆克文(Kevin Rudd)的顾问。
《观点》时事通讯是一份每周的观点总结,它将挑战、支持并告知你自己的观点。在这里注册
研究负责人迈克尔·切宁(Michael Chernin)和沙伊·哈勒维(Shai Halevi)在一份声明中说,“这座建筑是西方朝圣者的修道院和招待所,他们在墙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。”